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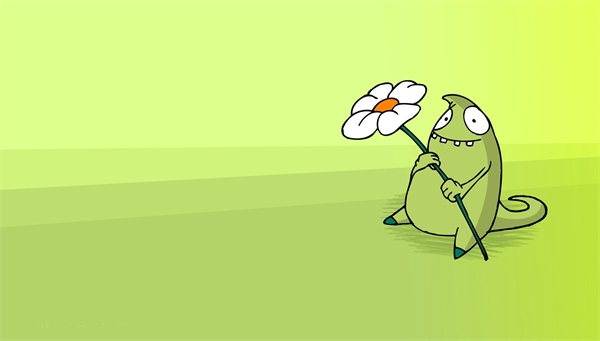
文 / 周文英
冬日的午后,闲散在阳台上,光线透过窗玻璃,洒在身上,融化了般舒服。想起多年前,家族近三十口人挤在一个u型院子里,我家房屋面北背南,冬天冷得像地窖,我和弟弟去三婆家的檐下晒太阳,小叔说太阳是他家的,不准我俩晒,弟弟抓住我的衣角,怯怯地往后退,母亲来了,三婆不好意思,夹一大筷头酸菜丢在母亲碗里,母亲夹点给我,转身去喂弟弟。尝到酸菜好吃,问母亲咱家咋没有,母亲说咱家没自留地,为啥没有?她不满的答去问你爷。
听母亲口气不好,没敢问爷爷,悄问慈爱的奶奶:咱家为啥没自留地?奶奶悠悠地说,你爷不爱地。可我分明感觉爷爷十分勤劳,爱地如子,他常说地是命根子呀。大人对自留地讳莫如深,便不多问。
从奶奶的片言之语中,逐知曾祖曾坐拥百亩平地,种着烟土,身材瘦削的他站在田间地头,望着罂粟花开如火,留着长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他面对大片壮观的风景,威武如临城的将军。
回到家里,曾祖父母坐在炕头悠闲地抽烟(鸦片),巧手的奶奶忙送上茶点,问晌午饭吃啥,曾祖父下圣旨般大手一挥说:臊子面!祖母领旨忙乐颠颠去做。
臊子面,当然是娘家在岐山的祖母做得好,面擀得又细又长,其他妯娌是插不上手的,奶奶凭一手好茶饭赢得曾祖的赏识,高兴却不敢表露出来,否则会招致嫉恨,只有更多操持家务。
土改,英明的曾祖早早缴出大片土地,虽然不舍,但和一家老小的性命前途相比,都是身外物。
爷爷当家时,只剩下十几亩地和一个长工,日子不算富裕,也属人上人,但安逸的生活却没有让父亲感受幸福,因家庭成分上学招工受阻,父亲好多次躲在牛棚里哭,恨我爷为啥占那么多地,为啥要雇长工,世上数你贪生怕死命贵。
集体农业社,爷爷的土地全部充公,分自留地,我家分到一星半点不长庄稼的边边角角。爷爷这儿挖那儿刨,垦出一绺菜地,但种的菜刚出土就被鸡呀狗呀糟蹋了,他割来枣刺,围起一圈栽蒜,蒜苗舍不得吃,只掐几片叶子当调料,地实在太薄,连蒜薹都长不出,结的蒜也是独瓣儿。
爷爷最舒心的事,就是种熟了一块菜地,但还没来得及享用菜地的瓜果,就永远地去了。
土地承包到户,勤劳的母亲顿感日月换新天,她像设计师规划蓝图一样谋划:大面积种粮食,水边地种蔬菜,坡坡畔畔种五谷杂粮,识字不多的母亲不会说“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”,只说人哄人地不哄人,谁对地好地就对他好。
她厚待土地,赶着节气时令播种施肥收割,不但让一家人吃饱还有了余粮,瓜果蔬菜样样都有,成了村人羡慕的对象,农民母亲,第一次有了尊严和成就感。
改革开放以后,紧跟时代潮流的父亲带wǒ men姐弟去南方打工,在城里买房,wǒ men成了最先扎根城市的农民,中国有词叫养儿防老,其实还应有词叫养儿帮小,为帮儿女照看下一代,父母跟随wǒ men,从一个城市漂去另一个城市,住的房子越来越高,离土地越来越远。出有车食有鱼的日子实现了,可母亲却越感空虚寂寞。
孝顺的弟弟懂得母亲的心思,买房时33层的高楼他选了二楼,给母亲说底层便宜,实际上是看中窗外的露台,母亲可以种菜。有段时间,母亲每天张罗着找泡沫箱,挖土,买种子菜苗,花铲,日子塞得满满的,回来还有见闻分享,wǒ men笑母亲也有了自己的事业。
夏天的早晨,太阳还没出来,母亲先去楼顶给菜们道早安,十几个箱子,葱椒蒜韭,黄瓜茄子,看谁需要浇水,看谁需要捉虫,哪里还有个空,要补棵苗,手里忙活,嘴也不闲,给辣椒边浇水边道歉:昨天提的水少,把你俩亏了,对不起,今早给多喝点。过一会又给韭菜说,你给咱长胖点,周六娃不上学,我割了好给娃包饺子,我圆圆就爱吃韭菜饺子。这一箱葱,上星期才壅的,底肥埋了豆渣,长得就是好。
菜们似有灵性,懂得母亲的絮语,个个都努着劲长,比赛似的水灵可爱。母亲自信地说,不管哪里,只要有土,就能种菜,感觉母亲生来就有农民天赋。
三十岁后,我不再为自己是农民的后代而自卑,感觉那些把菜种到国外花园楼下的中国父母,他们并不比农民高贵,因为他们种下的,不仅仅是可以食用的蔬菜,还有一份对泥土对祖国的情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