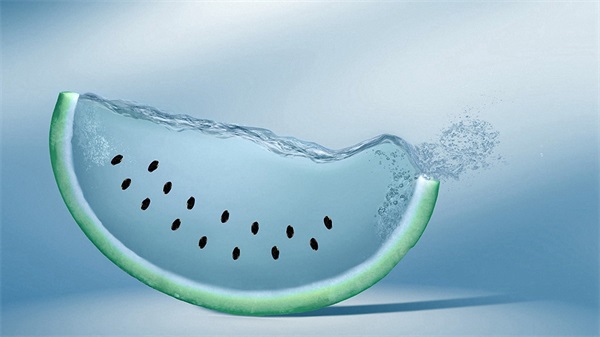我叫王石头,今年二十五岁,腾达保险公司业务员,湖南郴州人,性别?哦,性别男。
方脸平头的民警在纸上“沙沙”地飞快写下我的信息。我觉得此刻很温暖,有多久没人听我说过话了?“忘了在哪里看过,平庸无为的人被称为虫嗤,意思可能是虫子也嗤笑的人吧,我就是这么一个虫嗤。我的一切都透着两个字:——平庸,平庸的能力,平庸的外表家世背景,连姓名也很普通,‘王’是全国最大的姓氏,也就是许多人都姓王,石头,就是大街上任人踢来踢去的石头……”我说着,民警已没在听,转过头去询问这桩殴打事件的另一个参与者了。
空气中尴尬的氛围使我难受,我很想说下去,对着我脑袋里的许多观众,像电影的开头一样:男主角淡淡地叙说着自己的故事。酒精更懂我的情感,不像平日里的理智那么不许我表达,我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,“我想说下去,为什么打断我……”我酡红的脸上,肆意流淌着涕泪,警察同志被我冷不丁地发酒疯吓到了。
" 大叔,别恶心人了,"那个和我打架的十七八岁的不良少年冷冷地出声。白炽灯明晃晃地照着我和墙壁,这瞬间逼来的白使我的眼皮开始沉重起来。
那个和我打架的毛头小子叫李小崇,头上喷了不少定型水,抹了不少发胶的黄发竖成刺猬状,一脸上写满装出来的桀骜不驯。耳朵上戴着许多耳环,打架间我似乎拉拽过,伤口不住冒着血,汇成一滴泪珠状的红宝石。他也不擦掉,自我感觉像香港警匪片里流血的英雄。我才意识到自己也受了伤,往玻璃门一看,果然鼻青脸肿,颧骨那儿一大片淤青。酒精使大脑迟钝,这一觉才开始疼起来。
一个要下班的民警说,“小张,还没完啊?”那方脸的警察向那个年纪长些的说:"没呢,一个醉酒,一个倔的像头驴。"那人便走了,“老张”开始询 问wǒ men打架的缘由。
“为什么动手?”他望着我,手上的笔还停在讯问笔录的页面。我老实的回答:“我在酒吧兼职服务员,下班喝了点酒,走过仙霞路看见他和一个女孩在纠缠——看样子是他纠缠那个女孩了,看样子像要对那女孩不轨。其实若是平时的我,肯定不敢去‘英雄救美’的,我怕他有刀子之类的。但今天也许是酒能壮胆,我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和他打了起来。那女孩感激地看了我一眼才跑走了,一看就知道受了惊吓,我的猜测没错。”
李小崇有些着急,“谁说的,我只是去搭讪,可我也没干什么呀,就问问她的电话和住址……”老张抬头问他,“那你为什么要搭讪过路女孩啊?”他支支吾吾,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。这时,门口来了一个穿白色羽绒服的女孩,我大喜,正是刚才那个女孩。
老张神色庄重地说:“你这观念就不对了,你们年轻人就是不辨是非黑白。能传到群众耳朵的都是加了工的,说不定有人存心破坏祖国团结呢,你们这种观念很容易遭人利用啊。”
事情就这么和解了,我也没被拘留,还奇迹般地做了一件好事。走出警察局的门口,心情分外爽快。看着大上海的天空,幽暗深邃,繁星也格外明亮。其实我打架也不是为了英雄救美,只是为了找个人狠狠揍我一顿或让我狠狠揍他一顿……
上海是个不夜城,霓虹闪烁,灯火辉煌。黄浦江曼妙的身影在天空里穿梭,神秘的面孔上顶着黑眼圈和眼袋。这是个不眠的城市,也是个活跃的城市,她的活跃给出了可观的gdp,也给了我一份兼职——酒吧男洗手间的服务员。
洗手间需要什么服务呢?我就站在洗手间门口,脸上挂着虚伪的微笑,双手平端一个木盘,里面放着供客人擦手的洁白柔软的毛巾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直接装一个烘手机。然而从他们接受我面带微笑,见到客人90°鞠躬欢迎,递上毛巾等优质服务后愉悦的表情中,我似乎明白了:烘手机并不能带给他们像皇帝一般的尊崇感 。而我就是那个毕恭毕敬,卑躬屈膝的太监。
这只是经理跟我说的工作,但实际上卫生间所有的服务都得我去做。由于我优质的服务,客人们经常会给我小费,五元十元百元,一张张纸币红红绿绿地撒在我的木盘里,我当然得立即把他们收起来,否则就失去了服务员能变成钱的卑微。比起我那份固定只拿一千五百块的卖保险工作,这份隔三差五的兼职更像正职。
这里工作环境也好,卫生间宽敞,洁净,干燥而明亮。整齐的一排红外线感应站厕,白瓷在灯光下闪着纯洁的光芒,可惜却要被进来排泄的客人玷污了。那些人各个脑满肠肥,眼睛里闪着淫邪的光芒,这是两种多么不同的光芒!厕纸也是高级木材加工而成,触感特别好,这真是一间高级的酒吧。
我租的是许多人共用一个厨房、一个卫生间的老建筑,电视剧《蜗居》里海萍住的那种,卫生间里臭气熏天,方圆十里都能闻到浓烈的氨味。要到卫生间还有条冗长的走廊,黑魆魆的连盏小桔灯都没有。隔壁家的小女孩上厕所总要被吓哭,有次我看到她坐在走廊中间小声地抽泣,模样好不可怜。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和我一样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,脾气都不好,更别提守住人的骄傲。她有次大声哭,立即有人冲出来揍她一顿,然后与她的父母发生一场恶斗。其状如两条狗的厮杀:狂吠,撕咬红着眼,只怀疑他们是不是染了狂犬病。
所以能在这里兼职对我来说是买乐透中头奖一样的快乐——虽然我不知道中头奖的滋味,姑且让我这么比喻吧。换了班在这里解决人生大事也是一种幸福。
然而,今天却遭遇张明他们三人。张明是我的死对头,很快要升迁,和我不在同一组内,我和他素来不和。所以今天不去他的庆祝会也不单单是不想出钱,没想到他们会到夜色这么高级的酒吧,也没想到他们会碰见我……
我站在洗手间门口,垂首、鞠躬、微笑。外面五颜六色的强光跳动着、扫射着,音乐像发疯的巨人把大地震的像纵波来袭——咚咚咚,蹦蹦蹦,吉他手忘我地弹着吉他,一头长发甩来甩去;打击乐手用宛如朗朗一般飞快地手拿鼓棒敲击着金属;主唱撕心裂肺,几乎要把生命献给舞台。众人疯狂地扭着腰肢,尖叫声,劝酒声,调笑声……觥筹交错,每个人的瞳孔都是放大的。在这狂欢之中,赵诚,张明他们三人走向了卫生间,另一个我总不记得名字,许是他太有跟屁虫性格的关系。
我恨不能把头低到贴着地面,他们还是认出了我,一番羞辱是免不了的。赵诚拉了一下我红色的领结,谈了谈我青黑色的西装,“这不是王石头么,你怎么在这儿,不是在这儿当服务员吧……这儿的经理什么眼光,长成这样,一把年纪还能当服务员!”他神情具备地挖苦我,另一个说:“怪不得不跟wǒ men办庆祝会,原来是有事啊!”三人用比周星驰电影里的经典笑声还贱的声音一阵哄笑。
我挂上微笑,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请用。他们三个便去方便,张明说,“我的钥匙掉里边了,过来帮我找找,”我上前,蹲下视查——这也是常要提供的服务,显然是子虚乌有的事。张明给他们两人使了个眼色,他们一把摁下我的头,张明素手一摁,水喷涌而出,冲击着我的脸,我的头也全浸在水里,快不能呼吸,换气间吞了几口碱水。
头发在水里散开,我想起郴州老家的大水,那里因为是盆地常发大水。
庄稼稻田,房屋家禽,童年回忆,都被水淹没了……一场大水冲走了我的前程与希望,我成了大水后飘在水面上的被连根拔起的野草。我辍学,在这座城市漂泊,像孤魂野鬼。但没有一个人能去欺侮鬼,所以我活的比鬼还窝囊 。
他们终于放手,我抬头,猛烈的咳嗽。“看来是找不到了,wǒ men走吧。”临走前赵诚还给了我讽刺的一笑:“别以为自己多高贵。”我喘着气,这爱洁净的胃终是在心理作用下翻江倒海,“呜——呕——”。
我擦干脸,不顾客人或错愕或同情或带着莫名快感的表情,到镜前整理了一下,仍旧到门前挂着虚伪的笑容招呼客人。
我把工资全买了酒喝。喝得昏天黑地,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能身处灯红酒绿之中买醉。
“高贵?狗屁!没看到我的惨样。我只想攒钱重新有个家,有爸爸,有妈妈,有孩子……怎么了,怎么了?!上天为什么这么作践我……”我摇摇晃晃走出门,“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孤单,什么是寂寞”,我指着天空,“呜——打电话回家,不通,才想起他们不存在了。nǐ kàn,这街上这么多人,没有一个人和我有半毛钱关系,连个和我说话的人都没有!”
我蹲在路上呜呜地哭泣,一会儿指天,一会儿骂地。看着仙霞路上那些不正经的男找这种女人只会更寂寞而已。
天天都要经过这里去上班,经过这里回家,天天住在脏乱差的公寓,天天和计较一毛钱两毛钱的水费归谁出的妇女,敛眉大气都不敢出的中年男人住在一起。失败的人生,都是失败的人生!
大冷天,我走在马路上,踉踉跄跄。家长的水和马桶的碱水在我的脑子里浮现,屈辱感挥之不去,我的人生比那些人还失败。一种无望的感觉让我想找人狠狠揍一顿,或把我狠狠揍一顿,然后我就遇上了倒霉的李小崇在搭讪那个穿白色羽绒服的女孩。我冲上去实现我的渴望,揍在那人脸上就像揍在现实脸上。“wǒ men今天就一决胜负吧,要么我把你打死,要么你把我彻底打清醒,我再也不想在梦想与现实中逡巡。”那些几许还能找的回来。
直到有人把wǒ men拉开,然后不知怎么有人通知警察,然后被带到警局。被这么一打,我陡然明白张明,赵诚他们为什么讨厌我,因为他们早就选定了现实,看不惯我的犹豫,也看不惯我的懦弱,不满我死拖着不肯决断。
回到家我鞋也没脱就昏昏沉沉地倒在床上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头又沉又痛,像灌了太多水快被撑破的气球。往自己脑门上砸了三拳,短暂地中和了一会不适。呼出来的口气可以熏死三只老鼠。拿起搪瓷杯,牙刷,牙膏,一拧水龙头。那锈迹斑斑的水龙头失灵,再关不上,我颓然地垂下手,搪瓷杯咚地一下落地,发出一声叫人厌恶的闷响。
怒火一下子被点着了,我一脚踹开那个蓝色杯子,又踹了一下水龙头,把简陋房间里整齐的东西扔的乱七八糟。无力地瘫在地上,把头埋在雪白的水柱里,又想起了昨天。
水顺着颈窝流进后背,冰冷刺骨,衣服湿了大半。这么大的声响很久才把房东太太招来,因为这里平时就有很多人发疯摔东西,打小孩。
“哎呦,怎么搞成这样子哦,哝家也不容易啊,你们这些银啊!”上海话软的让人讨厌。我冷静下来,立起身:“打电话叫人修理吧,要有什么要有什么损失我会赔的。”
水渗到楼下,那家的那男女主人都跑上来质问,王八蛋狗崽子响成一片。周围还围了一些看热闹的人,幸灾乐祸地参与讨论,当做晨起的脑力训练。他们无人不精明也无人不喜欢精明。我还是在骂声中听到了手机铃声,循着声爬到床底下把它掏出来,甩了甩,机身上的水珠就形成圆润的珠子甩了出去。
“你好”,我的声音和我的身心一样累。打电话的是我的tóng shì,平时关系还不错。
“王石头,你负责的那位刘女士撞车死啦!她老公给她买的意外险才交了两千块,现在公司要理赔几十万,经理正在数落人呢。”
公司最近要裁员,保险这行本来竞争就大,现在出了这个事,我一定要被炒鱿鱼了。就算电话里不讲,我也知道这个意思,只是怎么会这么刚好。顾不得脚下打滑,身上还穿着又湿又臭的衬衫,抓起衣服就在一片声讨中离开了。
在公司的洗手间换了衣服,洗了无数遍脸,漱了无数遍口才去见经理。这个谢顶的男人正火冒三丈,见了我,只翕动着唇不停地骂着,我听不到他在骂什么,大概是平时不上进现在还害公司损失那么多钱吧。
他泛着油光的干瘪的脸上笑着,怒极而笑。然后把本就准备好的解雇信扔给我。我看了眼给我打电话给我的tóng shì,他立即低下头。我的眼眶湿湿的,我知道不会有人顾及我的尊严,泪腺再发达也要在此刻,忍住不能哭。
每个人对弱者都成了迫害狂。 备好的辩解没有说出口,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家。
像流浪汉一样躺在公园的长椅上,看着天空,白云悠悠地飘着,我早已没心情,也没那个才华去渲染这个场景,所以原谅我苍白的用词吧。
公园里的老者在吹奏《我心永恒》,笛子悠扬的声音催我入睡,梦境纷纭,足见我心神不宁。
我不知道自己的梦想,不知道自己能干嘛,假如有一个梦想可以坚持,我会毫不犹豫地抛弃现实,现实有什么呢?我的卑微不过给那些心理有问题的人取乐,一点意义也没有。
醒来时天空白得和梦里一样文艺,一个流浪汉静静地看着我,我忙起身。“对不起,我不是故意找你的位置。”他摇摇头,喉咙里呜呜作响,是个哑巴。
“在这里等很久了吗?”他想了想,点点头,孤独使我变得容易感动,又忍不住为他此举生出世界还是很美好之类的想法。
“喂,你们干嘛坐在我床上!”一个粗鲁的声音如雷霆乍惊,wǒ men两人一下,“这张椅子不是你的吗?”他摇摇头,对面过来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,这么孔武有力还当流浪汉。wǒ men对看一眼,飞快地跑了,他临走前还把口里的口香糖黏在椅子上,我忍俊不禁。
五年后,我成了一个不怎么出名的导演,没什么人记得我,我也没有在自己的作品中露脸的习惯。生活还是很穷困,有时导完一部戏口袋里的钱都被掏光却没什么收入,却一直生活得很快乐。又梦是另一种生活方式,从没人许诺有梦的人就能过上好生活。它不像人们想的那么脆弱和不切实际。
和流浪汉分别后,我把所有储蓄都去买了摄影器材和书籍,给人拍照,拍短片,凭借良好的态度和技术,近乎赔本的价格获得了许多机会,渐渐认识很多人,开始拍起了电影。
张明因为暗箱操作被捕入狱,一同的还有他的表哥,一个姓李的投保人。他们联合起来诈骗合约金。我去看他,穿着寒酸,他扫了我一眼,说:“还是混的个五年前一样。”我郑重的回答他:“不一样。”
他继续笑着,“你还不知道吧,你那位刘女士的车祸是自己故意的,所以不是意外,是自杀。买保险前查出有白血病,反正也救不活,不如用自己的死换一些保险金给老婆孩子花。调查这事的是我表哥,他说是意外就是意外,公司只能赔钱。”他见我没反应,继续说道:“觉得刘女士很伟大是吧,要自己迈向死亡,这需要多大的勇气。”又是一个误解勇气的家伙。他终于不理智了一回:“这么做根本没有错,有错的是人们的观念!我没有错!”
对张明这种反社会人格的人,我失语了,因为知道说什么都救不了他的偏激,我也不想当上帝。“诈骗是不对的,这种轻贱人命的行为更是不对的。”张明叹恨道:“庸人之见,活该一辈子活的那么懦弱。”他已不屑和我说话,对身边监守的警察说,“我说完了。”
警察就带着他走了,消失在长长的过道尽头的拐弯里。
注:这篇是高一发表在校报上的,文笔可能有些幼稚,请多指教